命运反讽在日常用语中指的是个人命运从顺境向逆境的突变。作为文学批评术语,它是后世批评家对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名剧《俄狄浦斯王》的基本剧情的概括。俄狄浦斯无意中弑父娶母,作为国王,他展开调查,最后发现始作俑者竟然是自己,他遵守诺言,刺瞎双眼,自我放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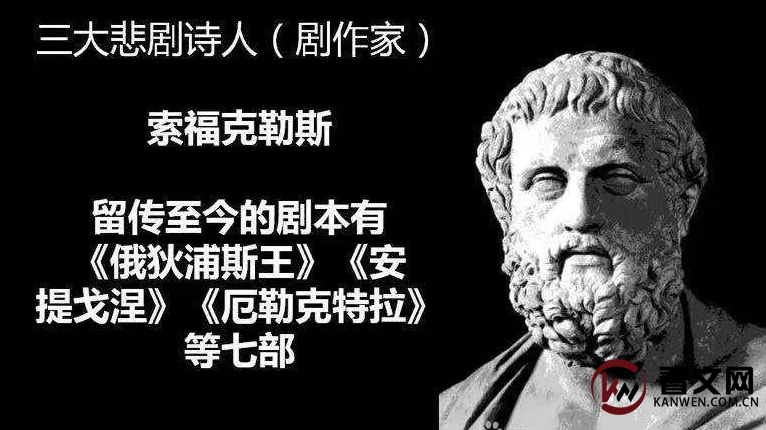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的叙事
俄狄浦斯发现自己是拉伊奥斯和约卡斯塔的亲生儿子,他无意中杀死了亲生父亲,娶了亲生母亲为妻。这一系列的发现让他感到羞愧和绝望。他为了面对过去的罪行,刺瞎了双眼,自我放逐。这就是命运反讽的经典体现。
在《俄狄浦斯王》中,命运反讽主要体现在故事的结构和双关语上。从结构上看,故事的发展完全出乎个体的预料,导致命运从顺境转向逆境,从而令人产生悲剧感。
命运反讽在文学中是一种强烈的表现手法,它让人们思考命运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生命中的无常和复杂。《俄狄浦斯王》作为一部经典的悲剧,成功地运用了命运反讽的元素,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深陷其中,对人性和命运产生了深刻的思考。
“突转”是指情节突然向相反的方向逆转,可以是从顺境到逆境,也可以从逆境到顺境,在悲剧中,往往是从顺境到逆境。然而,命运反讽并不止于“突转”,“发现”构成其不可分割的部分。亚里士多德如此定义:“发现,顾名思义,是从无知向知情的转变,是对应该获得幸福的人产生爱,或者对应该经受不幸的人产生恨。”
在这个定义中,“发现”不单单是发觉真相,它还有明确的伦理导向,也就是恢复人物的伦理向度,获得其应该有的评价。亚里是多德认为“突转”和“发现”应该共同使用,才能最大限度实现悲剧的震惊效果:“最精彩的发现往往伴随着突转。”我们可以说,没有“突转”的“发现”是缺乏力度的,而没有“发现”的“突转”是没有意义的。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笔者认为命运反讽应该同时包含这两个因素,而并非如昆杰斯所说的那样,命运反讽即突转。在《俄狄浦斯王》中,“突转”和“发现”几乎同时发生。该剧使用的是调查式的结构,即从最初的事实出发顺藤摸瓜,层层逼近真相。
所以故事“突转”的时刻便是主人公发现真相的时刻。如前所述,“突转”和“发现”发生于两个时刻,一是俄狄浦斯发现自己正是杀死拉伊奥斯的凶手,二是发现自己弑父娶母的事实。这两条线索共同构成了《俄狄浦斯王》一剧的命运反讽。但是,对事实发展情况的客观描述还不足以给予命运反讽以力度。
只有当主体意识和客观世界发生碰撞的时候反讽的意义才能凸显出来。俄狄浦斯王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是凶手,他坚定地认为自己不可能与此事有关,以至于当神谕说他就是凶手时,他执意认为是克瑞翁为谋取政权所下的圈套。俄狄浦斯的本意是好的,但他的好意最终导致自我的失败。
人对自我的认识和人现实的存在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反讽既是对这一反差的描述,也是对人的自我认知的质疑。同样,当神预言俄狄浦斯将弑父娶母时,所有人都在共同努力使这个预言破产。拉伊奥斯把还在襁褓中的俄狄浦斯交给羊倌处死,侥幸得救,并被波吕波斯国王收养的俄狄浦斯在听到神谕后,离开养父母尽力避免预言的实现。这一系列与神谕的对抗行为最终以失败告终。
人的所有回避命运的企图最终不能改变既定的命运路线,这一反差再一次强调人的主观性和客观事实之间的冲突。命运反讽不单揭示了命运的力量,同时也表现了因为自我认知的局限性而带来的主客矛盾,甚至是自我溃败。“发现”不光是发现事情的真相,也是发现自我的真相。
卡夫卡:K的叙事
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20世纪对命运反讽的认识和表现和索福克勒斯的时代有了很大的差异。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组成命运反讽的几个主要元素:对命运本身的呈现,命运加在个体身上的罪,个体为洗罪所做出的努力的溃败,个体和命运之间的和解。这些元素构成了《俄狄浦斯王》的框架,我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发现了同样的结构。
然而,相同的元素却有着不同的导向,如果说命运反讽本质上是人和主导性的外部力量间的关系的探讨,那么这种外部力量的性质的变化在20世纪直接导致了人和世界的关系的质变。《俄狄浦斯王》的命运反讽可以概括为:一个命定有罪而不知自己有罪的人采取一系列行为证明自己无罪,却最终发现自己有罪的过程。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命运反讽转变为一个被法庭判有罪实际上却无罪的人采取一系列行为证明自己无罪,却最终自我判定有罪的过程。同样的结构,不同的前提,卡夫卡的现代世界和索福克勒斯的古代社会相比,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悖谬之处,迷惑,恐惧,不可知是卡夫卡的命运反讽的基调。
在《俄狄浦斯王》中,命运以神谕的形式出现,它在一开始就被给出,清晰无误。在《审判》中,超验的命运失去了超验的特性,却保留了命运的威慑。这股力量被称为“法”,法庭是其具象的执行者。“法”的形象的悖诡之处在于它总是以社会机构的面目出现,但又超越单纯的物理意义成为主宰人、规范人、评判人、塑造人的无形的力量。
卡夫卡对不可捉摸、无法界定、无处不在、如影随形的“法”做了精彩的描述。在《审判》和《城堡》中,“法”既凌驾于生活之上又和生活混同为一体。审判K的法庭坐落在民居中,平时是木匠的住处,有审判时又成为法庭。同样,K寻求帮助的画家住的阁楼平时竟然也是法庭。
“法”的力量渗透到生活的角角落落,用来审判生活的法庭本质上又是生活的一部分。“法”与神旨不同的是,它不是超验的,它对人类世界方方面面的统摄使它成为人唯一的生存环境。泛法庭化的效果还在于K身边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和“法”相关:律师、画家、牧师、女人。
所有人都有可能是“法”的同谋或被告,人的本质属性不再依据其自身的品格给出,而是根据他和“法”之间的关系界定。“法”的悖论在于它与生活如此贴近,几乎和后者成为同一,但它和个体在根本上是隔绝的,个体无法洞见“法”的真面目,甚至连通向“法”的道路都不曾知晓,“在法的门前”的寓言和《城堡》就是人和“法”之间的关系的写照。
乡下人终其一生都在法门面前兜转,却始终未能窥见“法”的面目,最多看到了“法”的一束光。K面对城堡也是如此,他一次次走近城堡的企图都是原地打转。城堡全方位统治着村庄,却和村庄之间隔着一条不可穷尽的路。K这样描述城堡:“观察者的眼光始终不能集中在他身上,而只能从他那儿悄然离开。
这种印象,由于今天的暮色而变得更加强烈和深刻了;观看的时间愈久,愈不能看清他的真容,在暮色茫茫的时刻,一切都变得更加莫测高深了。”不管人是多么热切地想窥见“法”的真容,最后证明只是徒劳。问题并不在于人本身缺乏认识“法”的能力,而是“法”的隔绝和抗拒决定它终不可能和人产生直接联系,人的目光始终无法聚焦于“法”上。
正是这种既无处不在又无从接近的矛盾让人产生无力可施的绝望:“他想到,克拉姆离他很遥远,想到他那不可攻陷的住所;想到他的沉默,或许这种沉默只有通过大声嘶叫才能打破;而K从未听到过这种歇斯底里的狂喊乱叫,想到他那咄咄逼人的,眼睛往下瞪的,似假似真的眼神。
想到他的畅通无阻的道路,而K在下面不管怎样变着法子也无法阻拦他,只是根据不可理解的法律,才能见到昙花一现的道路;就此而言,克拉姆和老鹰才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法”的沉默面前大声嘶叫,面对他的召唤却无迹可循:K的绝望是无路可走的狂躁。正如卡夫卡的名言所云:“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
“法”的悖谬还体现在严苛和模糊并存。如同命运一样,“法”规定了每个个体在世界运行过程中的位置,个体只能根据他所在的位置行动。在俄狄浦斯王身上,我们还能看到鲜明的自由意志,神的绝对旨意不能改变人身上所具有的英雄气概,人被提到了和神同样的高度。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法”以先天的压倒性的力量控制了个人意志的生发,每一个以个人名义发出的行动都在法的布局之内,以K为代表的现代人几乎没有了行动的可能性。
卡夫卡这样描述法庭:“这个庞大的法院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是永远浮动着的,如果你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独自改变了什么,你就会丧失立足之地,从而会摔得粉身碎骨,而这庞大的组织却能轻而易举地在其他地方———因为一切都是关联的———为它所遭受的哪怕是最小的干扰找到补偿,不仅保持不变,反倒极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封闭,更加警惕,更严厉也更恶毒。”
个人会因为违背“法”的意志遭到毁灭性的惩罚,“法”却不会因为个体意志的对立损伤毫发,它的自我修复功能,它的补偿机制表明了任何以个人或集体名义挑战其权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恐怖的权力吸收了一切对立面成为壮大其自身力量的养料。
《审判》中K初次到法庭,发现观众分为两派,一派似乎是支持他的。最后他发现支持他的那派不过是为法庭工作的官员,他们根本上是法庭的人。“法”表面上包容异见,实际上是利用异见,甚至创造异见,为的是维持法庭正常运转的假象。
卡夫卡笔下的“法”不是一种原则,不代表任何价值,它是一部机器,一种规则,作为纯粹的力量被放置在自我运行的轨道上。它的唯一目的是自身的运转,只要永不停息地运转,一切有利或反对它的因素都可以被容纳进来,这使得“法”的面目非常模糊,不易被定性,这也是为什么K觉得很难集中注意力观察城堡。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法律的多面性被描绘得模糊不清,就像城堡官员克拉姆的形象一样。没有人真正了解他,所有关于他的观点都只是从各自的瞬间印象、想象和猜测中得来,导致人们对克拉姆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这种不确定性和迷惘在整个卡夫卡的作品中都是常见的主题。
即使有人声称见过克拉姆,也无法保证那个人就是真正的克拉姆,因为在卡夫卡的世界里,真相常常被掩盖。以假冒真,以虚代实在法庭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真相常常被模糊化,人们无法辨别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甚至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对是错。所有的接触和交往都充满虚幻和假象。
卡夫卡的世界中充斥着总体性的解体,而这种解体带来的是原则的缺失。虽然法律貌似控制着整个世界,但它却没有明确的原则,核心是空洞的,面目是模糊的。它虽然能产生一种威慑感,但其执行力却是荒谬的,让人感到迷惑和绝望。
观点:
这种虚妄的总体性原则加剧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异质性。环境不再成为人实现个人意愿的助力,相反,它成为了阻碍人发展、消磨人意志、摧残人本性的障碍。卡夫卡的作品中反映出人在异己环境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无助,他的命运反讽控诉着个体在无情环境下的绝望。在卡夫卡的世界中,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成为了永恒的主题。










